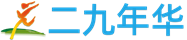《瓦格纳式的管弦乐法:现代性与创新》 ——让-雅克·威利教授系列讲座(二)
2019 年 11 月 13 日下午,法国巴黎索邦大学音乐学教授让-雅克·威利(Jean-Jacques Velly)于我院进行系列讲座《从瓦格纳到理查·施特劳斯》的第二场《瓦格纳式的管弦乐法:现代性与创新》。本系列讲座由我院主办,音乐学研究所、音乐学系和作曲系联合承办。
本场讲座一方面从前一场的主题——瓦格纳对剧场〓音效与音乐声学的追求——走出来,聚焦于音乐作曲本身的音响与音色实施;另一方面又与第一场讲座的主题有着密切的联系,即从音乐之内、具体管弦乐法的角度来探讨瓦格纳对音响的追求。
首先,威◥利教授以瓦格纳在1851年出版的论著《歌剧与戏剧》中的一句评论开启本场讲座:“一切对歌剧的形式施加真正、决定性影响的举措都源于独立音乐,这其实无关乎诗歌,而是音乐与诗歌的共同作用。”威利认为,这点无疑一语道破了瓦格纳对于那个时代风靡一时的歌剧体裁的总体评价:当时通行的歌剧体裁由于有失完美,而被瓦格纳无情↑地抛弃。他本人既是诗人,又是作曲家,所以他无法、也不愿将音乐与诗歌这两个因素割裂开。从19世纪初开始,声乐旋律在音乐诗意的表达方面已经远远逊于器∩乐旋律。于是瓦格纳宣称,音乐是戏剧真正的载体。他认为,在戏剧中,声乐旋律应跟随和模仿♂器乐旋律。但是同时代以罗西尼及其继任者为代表的意大利歌剧音乐却把器乐音乐作为声乐的伴奏,毋庸置疑极大程度地受到了瓦格纳音乐美学的批判。19世纪器乐曲的解放及其形而上学、独立音☆乐观念,既构成了瓦格纳音乐作曲的美学基础,又成为其在歌剧作曲中不断探索并丰富管弦乐技法的重要支柱。
“无处不在的戏剧表现”:柏辽兹配器法对青年瓦格纳的影响
瓦格纳对音乐、具体说来是器乐重要性的认识,在他的管弦乐写作方式上集中体现了出来。在其首次逗留巴黎期间,柏辽兹的配器法对他本人的配器观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他视柏辽兹为“贝多芬最有活力的直接继承人”、“我们音乐世界的真正救世主”。在青年瓦格纳的眼中,在这场戏剧风格与交响化风格的融合的艺术革新中,柏辽兹身先士卒,于是他很快便加入到柏辽兹的阵营中,并最终在音乐戏剧的层面上重新考量乐队的职能。从那以后,管弦乐艺术的新概念应运而生,它源于柏辽兹1830年的《幻想交响曲》。在瓦格纳的√观念中,作为和声的风向标,乐队“不再仅仅充当伴奏,而成了实现戏剧构思的工㊣ 具”。
瓦格纳早年对柏辽兹推崇备至,承认柏辽兹的实践让器乐语汇得到净化。但是他同时认为,这种净化还并不彻底,离完美还相距甚远。他认为只有言辞与音乐在戏剧中实现结合,建立某种打破了界限的音乐语言,灵活多样地探索各种配器的可能,才能够给予当时处于瓶颈期的器乐发展带来本质性的改变。瓦格纳对于歌剧革新的反思促使他重新思考乐队的作用和功能,因此他废除一切器乐的炫技,彻底反々思乐队的职能,使乐队专注地服务于“无处不在的戏剧表现”。
19世纪的乐器发展与瓦格纳的管弦乐法
接下来,威利教授以《黎恩济》的一段音频为例,着重强调了其中木管声部被提高了的重要性。
瓦格纳在其歌剧中配器的实践与改革,是与19世纪乐器形制的变化发展密不可分的。在19世纪,乐器形制的改良影响、乃至颠覆了器乐的创作手法和组合方式。管乐器的形制发展迅速,大大促进了瓦格纳自身观点的推进。木管乐器按键的贝姆系统与铜管乐器活塞系统的应用彻底改变了管弦乐队的音效,并奠定了现代交响乐团的基础。而这两种主要创新恰好伴随着瓦格纳最重要的音乐创作以及理论形成。从《黎恩济》到《帕西法尔》,瓦格纳终其一生引领了歌剧和交响乐领域的一次重要变革,这场变革正好促成了他用丰富的创作实践来阐明自己的理念。
接下来,威利教授播放几段音响,以举例说明乐器形制改良在瓦格纳管弦乐法中的体现。《唐霍伊瑟》序曲开篇的朝圣者主题主要体现了1830年代圆号的变革:新式圆号在原有自然音圆号的基础上加装了三个活塞,从而能够演奏半音阶。在《漂泊的荷兰人》序曲中,木管与铜管归功于乐器制作工艺的发展,获得了与弦乐器并驾齐驱的地位。在《女武神》中,铜管奏出的主导主题以琶音的形式出现,这与当时铜管的》传统手法高度一致,归因于瓦格纳从1855年的《女武神》起全面采用活塞式铜管乐器。
受法国学派影响,瓦格纳将铜管委以重任。按比利时音乐学家与作曲家格瓦特(Fran?ois-Auguste Gevaert,1828-1908)的说法,在铜管贡献方面法国人和瓦格纳“让铜管乐组真正实现音乐上的合奏,而不仅仅充当伴奏”。这点我们可以在《女武神》的主导主题中听到。在《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中,瓦格纳发表了他对圆号的如下看法:

“作曲家想通过圆号,来吸引听众的注意。毋庸置疑,引入活塞极大的提升了这件乐器的性能,这一重要的革新是绕不开的,尽管新式圆号不可避免地丧失了部分声音上、连奏上的美感。这一代价还是不容小觑的,特别是对那些很是希望保留圆号本质特〖征的作曲家而言,他本应▓尽可能地避免使用带活塞的圆号,如果他不清楚只有最杰出的演奏家才能逾越这一障碍。”
瓦格纳配器的三种方式
威利教授讲座的第三部分是瓦格纳的三种配器方式。他的配器从柏辽兹与梅耶贝尔作品中获益良多,分为“双管”、“三管”和“四管”三种编制类型。
“双管”编制的作品有早年的《黎恩济》、《唐霍伊瑟》和《荷兰人》。以《唐霍伊瑟》为例,弦乐在相同音高或高八度重复旋律,并以某些特定音型提供动能,为铜管主题伴奏;小提琴与中提琴的高音区能够奏出明亮的效果,而大提琴更富旋律性,并且不时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独奏段落;三支大管常常吹奏主旋律,这些特征也在《晚星之歌》中体现了出来。
在器乐大规模更新换代的年代下,瓦格纳决定性地引入英国管和低音单簧管,形成第二种配器类型——“三管”编制,代表作品有1848年的《罗恩格林》、1859年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1868年的《纽伦堡的名歌手》。威利教授在此以《罗恩格林》第一幕前奏曲的音响为例,他指出,该乐曲是管乐写作的范本,其渲染、烘托的某种超自然氛围,正是通过木管乐器在极高音区演奏产生的独特效果实现的:和弦似乎高高地悬浮在以太当中、悬浮在空气稀薄的平流层。此外,瓦格纳管弦乐色彩的和谐、杂糅以及音色的前后相续,都昭告着勋伯格意义上的、从一个乐器到另一个乐器旋律上体现出音色差异的音色旋律([德]Klangfarbenmelodie)的到来。
“四管”编制的代表作品是1876年的《指环》、1882年的《帕西法尔》。在这种乐队编制中,管乐组从配置到人数都翻倍了。瓦格纳还增加了自己发明的瓦格纳大号,并且混合圆号以及萨克号来演奏。威利教授分别用《齐格弗里德》、《众神的黄昏》以及《帕西法尔》中的音响举例,展现瓦格纳四管编制配╲器音色的丰富多样。
总结:瓦格纳式管弦乐法的美学内涵
瓦格纳的哲学思想体现在歌剧理论著作《歌剧与戏剧》中,威利教授借该著作中关于音乐与①戏剧的关系,从音乐美学的角度对本场讲座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总结。威利教授指出,这本书主要分为三部分:在“歌剧与音乐本质”部分,瓦格纳回顾并批判了过往的意大利歌剧,认为在其中音乐压№倒了诗歌;在“戏剧与戏剧化诗◆歌的本质”部分,瓦格纳指出戏剧化的诗歌应该反过来影响音乐的作曲;在“未来戏剧中的诗歌与音乐”部分,瓦格纳表明了自身的戏剧理想,诗歌与音乐要紧紧围绕着一个唯一的目的团结在一起,即形成独立的艺术作品。
在音乐戏剧创作的领域,瓦格纳坚※持认为“音乐本身无法思想;但它可以实现思想,也就是展现情感内容”。这表明了瓦格纳处于十八世纪末的哲学与音乐观念演化的历史潮流之中,这一潮流试图表明古代艺术中言辞在与音乐︾的互动中起着主导作用。然而,这一潮流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黑格尔、叔本华等哲学家都认为,音乐不受言辞的约束,为人的意识与其所处的现实世界打通沟通的渠道。
瓦格纳认为乐队是人声的回响,他坚持元音与辅音的区分。他认为,器乐发出的声音代表了人咿呀学语时发出的元音,每件乐器特殊的音响色彩则相当于辅音。瓦格纳通过音色游戏和元音与辅々音之间的“复调性互动”,并将合唱的功能转嫁到乐队,把乐队提升到支撑着主要言辞的高度之上,从而在音乐的戏剧中获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乐队的重要性就体现在,它需要提醒、预见、铺垫发生过与将要发生的事情,使听众注意力被吸引到音乐主题上来。瓦格纳将乐队的职能进行融合与升华,将之视为和声、甚至是戏剧动作整体的载体,因此上升为“可塑性极强的、由器乐演奏、蕴含千万变化的人物个性有机体”,与以往为歌唱伴奏的观念形成了天壤之别。由此,在歌剧中获得了主要□地位的乐队不仅是和声的载体,“而是成了一整部复调交响乐”。这才是瓦格纳通过极大程度进行管弦乐法创新后实现的音乐戏剧的美学实质。
不论是技术层面的管弦乐法还是形而上层面的美学理念,瓦格纳都对后世←的音乐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倾向于写作浓密厚重的乐队织体,而他的继任者理查·施特劳斯与勋伯格分别以自己的方式将之发扬光大。施特劳斯将瓦格纳视为十九世纪继柏辽兹之后的配器法改革者,并总【结的他在管弦乐法方面的本质特点:尽其所能地张扬多声风格、活塞系统带来的巨大飞跃、辉煌的炫技拓展到整个乐队。瓦格纳№运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将作品打上自己鲜明的烙印,对后世的音乐发展而言意义深远。
文:李沐颖
图:毛羽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二九年华大学门户 » 《瓦格纳式的管弦乐法:现代性与创新》 ——让-雅克·威利教授系列讲座(二)
相关推荐
- 我校郝维亚教授歌剧《萧红》首演成功
- 停课不停学丨张景丽老师带领学生用打击乐鼓舞信心!
- 今天,众声成城!我们为武汉放声!中央音乐学院携手兄弟院〖校师生千人合唱《我们》
- 7座金钟大奖!| 我校师生荣获第十二届中国音乐金钟奖比赛佳绩!
- 中央音乐学院交响乐团“高雅音乐进校园”成都巡演即将启幕!
- 平安校园 | 风雪中的校园守护者
- 央音师生为武汉加油丨劳黎老师:武汉,你好吗?
- 一念大意,前功尽弃!
- “之初”—— 中央音乐学院民族室内乐团于浙江音乐学院成功⌒ 举办专场音乐会
- 喜报 | 音乐人工智能与音乐信息科技系电子音乐作曲专业赵艺璇同学作品获得中英国际音乐节作曲比赛银奖
- 喜报丨附中李筱熹同学在第八届Severino Gazzellni 国际长笛大赛中荣获佳绩
- 中央音乐学院声歌系、北京嘉艺嘉和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钢琴捐赠仪式在鲁艺举行
- 俞峰:加强校际交流合作,促进国际音乐教育发展|我校校长会见多位外国音乐院校长
- 央音师生为武ω 汉加油丨声乐歌剧系17级本科班《为爱发声 武汉加油》
- 同心同行 再创辉煌 | 民乐系师生第十二届中国音乐“金钟奖”获奖实录
- 星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王秀明一行到访我校
- 学校贯彻落实教育部2020年“二上”预算培训会议精神
-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与高雅音乐的一次≡美好相遇!
- 央音校园,春暖花开!
- 停课不停学丨中央音乐学院纪念贝多芬诞辰250周年开幕式音乐会和你云端不见不散!
新闻公告
- 快讯!2020年研考国家线和复试安排公布 04-14
- 中央音乐学院定点扶贫工作推进会议召开 04-14
- 刘德海先生千古! 04-13
- 关于推迟举办2020北京现代音乐节的公告 04-13
- 央音战“疫” | 校领导亲切慰问抗疫一线同志 04-12
高考招生
- 中央音乐学院2016年本科招生简♀章 08-05
- 中央音乐学院2015年本科招生章程 08-05
- 中央音乐学院2006年招生简章 08-05
- 中央音乐学院2007年本科招生简章 08-05
- 中央音乐学院2013年招生计划 08-04
- 中央音乐学院2010年招生计划 08-04
- 中央音乐学院2012年招生计划 08-04